作者:黄锐,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
摘要: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基本假设 之上,社会工作理论的基本假设涉及到对人的假设、对社会的假设和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 假设。本文尝试将社会工作对人的假设定义为利他的人、对社会的假设界定为进步的社会,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假设确定为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澄清社会工作理论的哲理传统与价值取向,也对建构社会工作的一般理论乃至于社会工作学的构想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在社会工作的百年历程中,社会工作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担当着先导角色。仔细检视现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后不难发现,这些社会工作理论大多探讨的是怎么做社会工作,也就是西本(Roger Sibeon)意义上的关于如何开展社会工作的理论,或里斯(Stuart Rees)意义上的策略理论(Strategic Theory),或福克(JanisFook)意义上的实践理论(Theories of Practice),或大卫·豪(David Howe)意义上的社会工作的理论(Theoryof Social Work)。的确,这些社会工作理论涉及到处置原则、干预过程以及实务技巧等,有助于开展社会工作实务,但同时或多或少疏漏了社会工作理论在理论建构层面的探讨,比如社会工作理论的基本假设、核心概念等。
一般而言,社会工作理论涉及到对人的假设、对社会的假设和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假设。令人诧异的是,我们一直对此缺乏明确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不利于社会工作实务的进一步发展,也难以推动社会工作一般理论的建构,甚或影响到了社会工作学的构想。笔者以为,个中原因或许与社会工作长期坚守的实务取向有关。有学者分析指出,“一提到理论,社会工作要么直接忽视,要么嗤之以鼻。理论是深奥的、抽象的,只有在大学教育中才会被提及,而实务则发生于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是常识性的,是具体的。社会工作被许多人视为是一个以实务为中心的专业,与理论并无直接关联,甚至将导致社会工作的实务本质模糊不清。在许多时候,理论远远没有社会工作者的应急反应和个人品质重要”。
的确,社会工作是以实践的方式回应社会中的健康、环境、福利、社会正义等复杂性、结构性议题,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认识到,社会工作不能缺少理论,尤其是社会工作的处置原则、干预过程以及实务技巧等皆有其社会理论的脉络。因此,本文尝试将社会工作置于社会理论之中,探讨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一些基础性问题。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基本假设之上。本文尝试将社会工作对人的假设定义为利他的人,对社会的假设界定为进步的社会,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假设确定为个人与社会。
二、利他的人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人的假设是“经济人”,即追求个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为直接而且重要的体现是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分析以及边际革命;社会学对人的假设是“社会人”,即马克思所提出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少学者提出,社会工作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社会互动,或称之为一种“制度化的利他主义”。正如鲁伯特(Roy Lubove)所指出的,社会工作者是“职业的利他主义者”。或者说,“社会工作职业的存在就是为了使某些具有利他意图的政策得到执行,并且惠及大多数人”。在此意义上,社会工作对人的假设是“利他的人”。
我们倾向于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最先创造了利他(altruism)一词,指涉的是“一种为他人而生活的愿望或倾向”。但早在“利他”概念被提出之前,已存在不少的对于“利他”的思考与探索。比如,康德所倡导的义务哲学强调,“我应该努力提高他人的幸福,并不是从他人幸福的实现中得到什么好处。不论是通过直接爱好,还是间接理性得来的满足,仅仅是因为,一个排斥他人幸福的准则,在同一意愿中,就不能作为普遍规律来看待。”
一般而言,利他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亲缘利他、互惠利他与纯粹利他。亲缘利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是为亲属做出某种不含有功利目的的牺牲。目前,这已被生物学家所证实,是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中一种普遍且稳定的行为,也被称为“硬核的利他”(Hard-core Altruism),指涉的是一种“亲缘选择”(kinSelection)。互惠利他是不存在血缘纽带的生物个体为了今后获得相应的回报而提供某种帮助,也被称之为“软核的利他”(Soft-core Altruism)。对此的解释涉及到博弈论和生物演化论,特里弗斯(Robert Tr ivers)最先运用囚徒困境博弈建立了互惠利他的自然选择模型,后来史密斯(Maynard Smith)和普莱斯(G.R. Price)结合了经典博弈论和生物演化论,提出演化博弈的基本均衡概念——进化稳定策略(ESS)。
纯粹利他是不存在血缘纽带的生物个体在不追求任何回报情况下的行为。一大批主流生物学家从个体选择理论出发,基于现代基因技术和遗传学,否定了纯粹利他。正如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所提出的,“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即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这一基本的遗传单位”。并且,“如果你认真研究自然选择方式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凡是经过进化而产生的都应该是自私的。……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共同的利益’是毫无意义的概念”。桑塔费学派的学者则认为,这是一种“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行为,是为了维护他人与团体利益,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为前提, 惩罚那些破坏合作的生物个体的行为,也称之为利他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或“亲社会情感”(主要包括同情心、愧疚感、感激心和正义感)。赫伯特·金迪斯(Herbert Gintis)和萨缪·鲍尔斯(Samuel Bowles)建立了复杂的仿真动力学模型,并且使用计算机仿真模拟了这一过程,结果表明:强互惠或利他惩罚可能存在某种生理基础,即强互惠或利他惩罚可能与人的大脑神经结构中的某个神经中枢密切相关。后来,这进一步被脑成像的证据证明是大脑神经结构中一个被称之为“尾核”的神经中枢。此外,鲍尔斯和金迪斯还使用大量的实验、考古、基因学和人种学的材料分析族群中的人如何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而维护族群伦理和帮助他人,建立了一个共同进化的模型,揭示出人类的合作及其演化机制。
社会式作所强调“利他的人”更多指涉纯粹利他,与贝克所倡导的“利他个体主义”类似。 利他主义是一种“将个人自愿及个性与帮助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新伦理。……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而活,同时,每个人又都必须保持高度的社会敏感性”。甚或,这体现出“给予却不必牺牲自己”的原则。
三、进步的社会
最新的社会工作全球定义表明,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是推动社会改变和发展、社会凝聚以及人民的充权(empowerment)和解放;首要原则为尊重人与生俱来的价值和尊严,不对人造成伤害,尊重多元,坚守人权和社会公义。这既意味着社会工作将人的尊严、价值、需求、社会改变及社会正义置于优先地位,同时也表明社会工作以某种道德的意味规定了社会的进步方向。质言之,社会工作对社会的假设为进步的社会。然而,一提及进步,我们难免不陷入深深地沉思之中。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第一次提出并阐述了社会进步的观念,与此伴随的是对社会进步的质疑。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出历史进步论,试图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的分析,揭示历史在总体上的进步。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在《论人类精神的持续进步》中提出,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把人类历史的进步理解为知识的进步,即神的崇拜、再造新神和科学知识。孔多塞在伏尔泰和杜尔哥的基础上撰写《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把历史划分为人类结合成部落、游牧民族由这种状态过渡到农业民族的状态、农业民族的进步下迄拼音书写的发明、人类精神在希腊的进步下迄亚历山大世纪各种科学分类的时期、科学的进步从它们的分类到它们的衰落、知识的衰落下迄十字军时期知识的复兴、科学在西方的复兴从科学最初的进步下迄印刷术的发明、从印刷术的发明下迄科学与哲学挣脱了权威的束缚的时期、从笛卡尔下迄法兰西共和国的形成和人类精神未来的进步等十个时代,勾勒出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观。与此同时,卢梭非常敏锐地观察到进步所带来的未预期的恶果,比如,“科学与艺术的进步不仅没有起到敦化风俗的作用,不但没有给人带来幸福,反而败坏了社会的风尚,造成了人类的不平等,带来了无数的灾难,导致了人类的没落。”
进入19世纪中后期以后,进步成为普遍的时代观念,然而对进步的批评也从此愈加严肃,尤其是人类遭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学者对付出惨烈的代价而获得的进步深表怀疑。以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为例,他受卡尔的历史进步观极深,早年坚信“从长时段来看的话,社会史学家必须研究历史上基本的动态因素——社会生产的进步过程。就其涉及的范围而言,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社会生产的进步是由历史发展所造就的。”他在“十九世纪三部曲”之一的《资本的年代》导言中写道:“本书叙述的历史是一边倒的历史,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在《帝国的年代》的结语部分,他满怀悲怆的笔下写出,“就人类的物质进步和对自然的改造而言,20世纪似乎比19世纪更令人信服。……然而,我们有充分理由不再把人类历史置于进步的轨道上。原因在于,甚至在20世纪所获得的进步已绝对无可否认的时候,却还有人预测人类未来不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时代,甚或马上大祸临头:另一次更致命的世界大战、生态灾祸……。这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教会我们活在对天启的期待之中。”从20 世纪80年代开始,对进步幻象的讨论在后现代思潮中达到极致,与此同时也有学者重整进步的叙事。比如,平克(Steven Pinker)新著通过大量的实证材料,“把人类历史中各种减少苦痛、要求人道、追求解放的历程连贯成一个完整的进步叙事,不啻为道德意识建立了一套演进史”。
以上的讨论最终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还能持有“进步”的观念吗?如果能的话,那么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过程,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如果不能的话,我们有可能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站在社会工作的立场上,我们应当在承认社会进步、道德进步的意义及其问题的同时,赋予进步新的意涵。首先,进步具有规范性。著名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提出,“进步思想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这种思想断定,进步已经发生了;它也断定,进步应该发生,而且一旦阻碍进步的障碍被排除以后,它就会出现。这些障碍便是人类一味依恋过去的陈腐习惯和信仰。”因此,“进步”既是对于以往历史经验的归纳,又同时是对未来的一种预测,具有两重性而非二元性。其次,进步具有道德导向。金斯伯格(MorrisGinsbery)指出,“贯穿所有时代的进步理论的核心,是相信人类已经前进、正在前进并且将继续前进,最终实现对人类伦理需要的满足。”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个体将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增进自身的德性。再次,进步意味着相信个体理性。自启蒙运动以来,个体理性作为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潜力被发掘出来,构成进步的微观基础。正如希尔斯所论述的,“进步思想以一种世俗化的翻版接受了关于人类堕落以及通过上帝恩典加以救赎的思想传 统;以后这个传统中又增加了人类精神日益自我实现进化的思想。人类精神进化的思想逐渐变成了社会进化的思想,其目标是在更为完善的人类世俗生活中实现精神的潜力。”最后,进步并不指向一个外在的目标,而是同时聚焦个人主体性与社会自主性,回归个体的反身实践和社会的道德逻辑,展示丰富的可能性。
四、个人与社会的统一
长期以来,个人与环境/ 社会的互动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建构,甚或直接表现为生态系统视角。遗憾的是,如何界定这一互动关系?梳理社会工作发展史不难发现,个人与环境/社会的互动在本质上体现为两者的统一性,即个人与社会的统一。这可以追溯到格老秀斯(Hugo Grotius)。他从个人的社会性或称之为社会欲望寻找“自然法”的基础。不过,他所谈论的个人已经不再具有原始的单纯,个人与个人之间也难以产生“相互的爱”,而是只能通过财产权利确立“属己”的领域,进而实现对社会的守护。与此同时,“社会就是要努力实现,在共同体的活动和协作下,每个人完好地享有他自己的”。因此,个人的社会性表现为“共同体的活动和协作”,社会的个人性则是“每个人完好地享有他自己的”的体现,两者的联结则建立在财产权利基础之上。普芬多夫(Samuelvon Pufendorf)延续了格老秀斯的讨论。不过,寻求自爱或自我保全要求个人必须和同伴相互协助。由此,个人与个人之间保持了一种自爱或自我保全所要求的“社会性”。换言之,“那些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可能、应该、而且经常习惯于过着社会的生活” 。
到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分工论》那里,这句话反转为“为什么个人越变得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在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却越加紧密”。涂尔干指出,“劳动分工的最大作用,并不在于功能以这种分化方式提高了生产率,而在于这些功能彼此紧密的结合……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出了纯粹经济利益的范围,构成了社会和道德秩序本身。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只有分工才能使人们牢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联系”。因此,“劳动越加分化,个人就越加贴近社会;……社会能够更加有效地采取一致行动”。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尔干更进一步论证社会不仅超越于个体存在,又存在于个体之中。首先需要声明的是,他对于澳洲的原始宗教研究,“并不是出于猎奇,而是要在最简单的社会里探索人类社会的奥秘,以便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改革的要求”。涂尔干指出,“图腾制度不是关于动物、人、或者图像的宗教,而是关于一种匿名的和非人格的力的宗教;它见诸于所有这些事物,而又不与其中任何一个相混同,谁也不能完全拥有它,但又可以分享它,它完全独立于它所化身的对象,既先于该事物而存在,又不会随之消亡。个体死灭,世代交替,但这种力量却总是真实、鲜活、始终如一的。它把生命力赋予今天的一代。就如同它昨天把生命力赋予了上一代一样,而明天一如仍是。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它是每种图腾所敬仰的那个神,但它是非人格的神,没有名字或历史,普遍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上,散布在数不胜数的事物之中”。他批评泛灵论,强调“没有什么东西因为它的本性就一定会高高在上,成为圣物,但同样也没有什么东西就必然不能成为圣物。一切都取决于导致创造出宗教观念的情感究竟是确定在这里还是那里、在这一点上还是在那一点上的环境”;批评自然崇拜,认为神圣性“是被添加上去的,宗教事物的世界不是经验的自然界的一个特定方面,它是被加在自然界之上的”。并且,澳洲人在集会中所形成的集体欢腾,不仅建立起他们对宗教的神圣态度,而且也同时引向神圣的世界,即社会之独立及其神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澳洲人通过禁忌、成年礼、苦行,将神圣事物与凡俗事物分离,消除人身上的凡俗性一面,同时与神圣事物建立联系,培养个体的宗教性和道德性,即个人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涂尔干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最终导向的是共生关系,“没有神,人就不能生存;不过另一方面,如果人不进行膜拜,神也会死去”。或者说,社会“只有在个体之中并通过个体才能存在和生存。倘若个体心灵和信仰中的社会的观念消失殆尽的话,群体的传统和宏图就不会被个体感受到,不会为个体所分享,社会也就寿终正寝了”。简言之,“没有个体就没有社会,一如没有社会也就没有个体”。
其实,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可以和中国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相对应。按照费孝通的理解,“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社会’,也是‘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和‘自然’合一的”。而“人的一切行动和行为,都在‘天’的基本原则之中,人不能彻底摆脱、超越这个‘天’的,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同时,天也随着人的行为而不断做出各种反应,故有所谓‘天道酬勤’、‘天怨人怒’之说。”费孝通进一步引申为,“对于‘人’和‘自然’的关系的理解,与其说是一种‘观点’,不如说是一种‘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对所有客体的态度,是‘我们’对‘它们’的总体态度。这种态度,具有某种‘伦理’的含义,决定着我们‘人’如何处理自己和周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从我们‘人’这个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其实也构成一个‘差序格局’。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把我们人和人之外的世界,视为一种对立的、分庭抗礼的、‘零和’的关系?还是一种协调的、互相拥有的、连续的、顺应的关系?”
五、小结
利他的人、进步的社会最终指向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因此,这意味着社会工作实务进一步聚焦服务对象需求,推进利他介入,最终在助力服务对象个人改变的同时实现社会的进步。对于社会工作一般理论的建构而言,以利他的人、进步的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等三个基本假设为基础,甄别出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的核心要素,进而阐明社会工作的基本动力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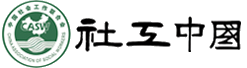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