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一群十多岁的女孩儿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出路在哪里。
深圳市一家叫做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厂里,这群女孩儿每天工作12小时,换取每月2000元的工钱。由于不满16岁,她们的工作被法律禁止,雇佣她们的企业和她们的监护人,须为此负责。
她们身后,是近乎绝望的景象——在家乡四川凉山,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区,“孩子简直像牛羊一样被放养着”。全家一年的收入,往往只相当于她们在深圳一月所得。
当聚光灯打来,一个由公安、劳动、应急等部门组成的10人护送队伍,浩浩荡荡地陪同她们踏上返乡之路。凉山州政府也“组织相关部门到火车站迎接孩子”。看起来,一切都朝着圆满解决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这条路上,女童踟蹰不前。在新闻镜头里,她们一路飞奔躲避记者,在劳动部门的检查下,她们“结成同盟,不承认自己是童工”。
“不想回家,回家每天就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深圳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饭和肉。”临行前,一个女孩儿的话让她们即将踏上的道路更加模糊。
“这下孩子们断了财路,过得好谁愿意出来打工?”“让这群孩子怎么办,媒体不该这么报!”在这个令人唏嘘的故事里,人们迅速找到了指责对象。
这种非议并不陌生。当北京“井底人”王秀青的报道带来封井的铁锹,质疑的声音和此时几乎毫无二致。
批评者的理由简单直接:凉山的贫穷不能指望一夜转变,孩子的碗里也不会凭空多出肉来。与其让她们在山里遭受更大的苦,倒还不如容忍她们在现代化的城市里有个栖身之所,“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是须知,社会的进步并不能靠与现实的妥协推动。必须坚守的一个底线是,即使再贫困,这些迷失于高楼间的童工,也应当安坐于课堂上,即使用工再紧张,企业主和劳动部门监察人员也不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童工出现在嘈杂的车间里。
所幸的是,聚光灯并不总是带来坏消息。当王秀青居住的热力井被混凝土封住,他很快被北京的一所学校录用为保安,走进了明亮的宿舍,这才让参与报道的记者松了一口气。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随之松一口气。
至少,那些踏上归程的童工们,还在担心,没有挣到工钱,很对不起攒了好几个月钱才凑足500元路费的父母。
那么,到底谁该为女童的进退维谷负责?贫困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但这是一个更大的维度。在这广阔的空间里,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能轻易找到为自己开脱的理由。
接到举报便迅速出动,甚至派人陪同女孩儿遣返,深圳市劳动部门堪称雷厉风行。但女孩儿们不愿踏上回家路,或许是因为她们不知道,回家之后会是怎样一幅图景?也或许是因为她们知道,一旦聚光灯暗去,她们的生活又将重陷黑暗,甚至再次出山打工。
2008年,东莞雇佣凉山童工的现象就曾被媒体曝光。聚光灯打到之处,恰如今日之景:凉山州政府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飞赴东莞解救童工”,东莞市委书记也“亲自批示”。不过,聚光灯忽然灭掉,一切也就归于平静。依稀还能见到的,是一篇刊发于《凉山日报》的报道,称凉山州喜德县,“适龄儿童基本上没有因为贫困而入不了学”。
那里,正是这次被遣返的童工的故乡。
聚光灯亮时各路人物就粉墨登场,灯光黯淡,也随之悄悄离去。政府对新闻报道的这种应激式反应,或许才应为童工的不愿回家负责。
而且,这样的心态不止存在于凉山州或东莞市。当河南郑州饥寒交迫的农民工在高架桥下死去的消息进入人们视野时,阻挡农民工桥下露宿的花盆和栏杆一夜之间出现,但是转眼寒冬又至,有谁注意到那些新闻之后建立的“零工信息服务站”,大多已经荒废成摆设?
即使在那个看起来圆满的“井底人”的故事中,也不难觅其踪迹——早于王秀青十年前,就有一名叫做老于的老人同样住在热力井中,媒体的曝光为他带来了妥善安置,却没有人继而想出办法提前阻止更多人爬下黑暗的井底。
“十年前的一次记录,帮助井底人走出来,过上正常生活,却没能帮助这一现象的改观。十年后的今天,记录的媒体多了,这样的一次围观最后能带来什么效果,我不知道。”在王秀青遇到他的美好结局前,曾有人如此悲观地写道。
其实答案很简单。围观本身并不能真的带来改变。聚光灯终会暗去,人群也将纷纷离场,若这时仍有一些人留在原地忙碌,解决问题的出路,或许才能真的由此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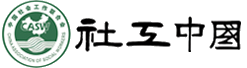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